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:四十年回望里的红色印记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那个暑假,我还裹着大病初愈的虚弱,被哥哥接到水口山区公所。彼时的阳光总带着点昏黄,透过矿区高耸的井架洒下来,在红砖平房的墙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哥哥白天忙着公务,傍晚便会牵着我的手,穿过冷清的街道往工矿区走。那些日子,成了我往后四十年反复咀嚼的回忆——像康家戏台的木柱上刻着的年轮,每一道都浸着时代的温度。
一、红砖平房里的少年心事
第一次见到康家戏台时,它还不是后来被圈起来的“景点”。清同治年间的木构戏台爬满了青苔,檐角的铜铃在风里晃荡,声音能传到半里外的工人宿舍。哥哥告诉我,1922年冬天,3000多个矿工就是在这里挤得水泄不通,攥着拳头听人宣读“湖南省水口山工人俱乐部”的章程。“你看那戏台板上的凹痕,”他指着台面被磨得发亮的木纹,“都是当年工人踩出来的。”
那时的工人宿舍是连排的红砖平房,墙缝里长着野草,屋檐下挂着职工们晒的萝卜干。我常趁哥哥不注意,溜进宿舍区看他们下棋。老矿工们总爱蹲在门口的石墩上,手里捏着搪瓷缸,讲起罢工的往事眼睛就发亮:“毛主席当年住过康汉柳饭店呢,就在戏台后面,穿件蓝布长衫,跟咱们工人一起蹲在地上吃红薯。”他们说的饭店,我后来偷偷去过,土坯墙配着黑瓦顶,门框上还留着模糊的“安寓”二字,风一吹,仿佛能听见九十多年前的脚步声。
工人剧院的木板门总吱呀作响。傍晚时分,里面会传出样板戏的唱腔,《红灯记》里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的调子,能穿透半条街。我最羡慕那些能凭工作证进去看戏的工人,他们胸前的徽章在路灯下闪着光,脸上是我读不懂的自豪。有次生病,哥哥带我去工人医院,白墙白床的诊室里,医生摸了摸我的额头,说“矿工子弟看病不要钱”。那一刻,我望着墙上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标语,心里突然生出个念头:长大了一定要来这里当工人,住红砖平房,看工人剧院的戏,让那枚闪亮的徽章别在自己胸前。
可命运偏要留个遗憾。那年水口山招工,大队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,我甚至连夜缝好了新布鞋,却在最后关头被刷了下来。哥哥蹲在水口山区公所的门槛上,摸了摸我的头说“以后还有机会”,可我知道,有些错过就是一辈子。后来每次路过县城的招工公示栏,我都会盯着“水口山”三个字发呆,直到字迹被雨水冲成模糊的蓝痕。
二、四十年后的重逢:从矿洞到厂房的蜕变
2019年七月,当文联的中巴车驶过水口山高速路口时,我攥着扶手的手突然发起抖。窗外的景象陌生得像另一个世界——昔日的红砖平房被整齐的厂房取代,高耸的井架换成了银白色的冶炼塔,连空气里都少了当年的煤烟味。同行的艺术家们笑着说:“这哪还是老矿,分明是现代化产业园。”
走进八厂的车间,安全帽的系带勒得我下巴发紧。全自动化的流水线在眼前铺开,机械臂精准地夹起铅锭,传送带载着闪烁的锌块无声滑行。四十多年前见过的人工熔炉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电脑监控的温控系统,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代替了工人额头的汗珠。陪同的技术员指着一块银光闪闪的金属板说:“这是电铅,纯度能到99.99%,以前人工炼十炉都出不了一炉这么好的。”我突然想起老矿工们布满老茧的手,他们当年用钢钎凿出来的矿石,如今正通过这些精密仪器,变成能远销海外的产品。
在瓦松铁路公司的调度室,巨大的电子屏上,运矿列车正沿着铁轨缓缓移动。“以前运矿石靠人推矿车,现在一条铁路直通长江码头。”负责人的话让我想起忆苦窿——那个藏在山坳里的老矿洞,六七十年代还作为教育基地开放,里面摆着背篓、油灯和锈迹斑斑的铁锤。我最后一次去时,洞口的木牌上写着“1990年封洞”,如今想来,封起的是落后的开采方式,启封的却是一个产业的新生。
五矿铜业的厂房里,电解槽泛着幽蓝的光,铜离子在电流作用下凝结成紫红色的铜板。“咱们水口山的矿,铅锌金银铜全有,光铅锌储量就270万吨。”同行的老作家感叹,“当年毛泽东考察时说这里是‘宝藏’,果然没说错。”我望着墙上“中国铅锌工业的摇篮”几个金字,突然明白:那些年在红砖平房里听来的故事,从来不是封存在过去的传奇,而是正在续写的篇章。
三、三次朝圣:红色殿堂里的精神接力
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就立在高速路口对面,从空中往下看,像一块被劈开的巨大矿石——设计师说,这造型是“工人”的“人”字与矿石的结合,象征着被压迫者的觉醒。7023平方米的馆区里,2865平方米的展厅藏着比我记忆更厚重的历史。
第一次走进纪念馆,是2024年5月跟着全国著名作家杨晓敏一行。那天阳光正好,常宁作协的会员们围着讲解员,在“水口山工人运动史陈列”厅里驻足。玻璃柜里的老物件让时间倒回:1922年罢工用的铜锣,锤柄上还留着矿工的指痕;耿飚少年时用过的矿灯,玻璃罩上布满划痕;还有一份泛黄的《罢工宣言》,字迹被岁月浸得发暗,却字字透着“我们要吃饭”的呐喊。杨晓敏老师指着一幅版画说:“这些矿工不只是历史符号,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觉醒者。”那天的座谈会上,有人念起耿飚的回忆录:“在水口山的童工生涯,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压迫,什么是反抗。”我突然想起红砖平房里的老矿工,他们讲的故事,原来都刻在这些文物里。
第二次是2025年3月22日,陪桐黄完小的党员们来开展党日活动。三十多位党员老师在馆前的广场上重温入党誓词,声音震得枝头的露珠都落了下来。在“耿飚生平业绩陈列”厅,年轻教师们围着展柜,看这位从水口山童工成长为外交部长的革命家的遗物:补丁摞补丁的工装裤,在苏联留学时用的笔记本,还有1981年回水口山时与老矿工的合影。“原来伟大的人,起点和我们一样平凡。”一位年轻老师轻声说。当走到“八百矿工上井冈”的场景复原区时,灯光突然暗下来,投影里的矿工们扛着钢钎前行,脚步声在展厅里回荡。有位老教师红了眼眶:“这些人里,说不定就有当年在工人剧院唱样板戏的矿工后代。”
第三次是今年6月下旬的一天,跟着常宁民间演艺圈的伙伴们。新世纪剧团的演员们穿着戏服,在“矿冶历史陈列”厅里对着老照片比划——他们要排《八百矿工上井冈》的新戏。福运来演艺的琴师抱着二胡,在康家戏台的复原场景前拉了段《映山红》,琴声绕着木质的梁架盘旋,恍惚间,仿佛能看见1922年的矿工们正仰头合唱《国际歌》。“我们要把这些故事唱给更多人听。”团长拍着我的肩膀说。那天离开时,夕阳正照在纪念馆的玻璃幕墙上,折射出的光落在不远处的文旅小镇上——那里新开的民宿挂着“矿工主题”的招牌,卖纪念品的店里摆着复刻的老矿灯,红色的历史正变成鲜活的生活。
四、尾声
从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走出时,日头已偏西。纪念馆的轮廓在暮色里渐渐柔和,那些玻璃柜里的老物件、墙上的照片、复原场景里的光影,还在眼前晃。风从冶炼厂的方向吹来,带着点金属的凉意,混着远处文旅小镇飘来的饭菜香,倒像是把过去和现在拧成了一股绳。
想起七十年代初那个暑假,老矿工蹲在石墩上抽烟,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,说“咱们工人的骨头是硬的”;想起2019年在八厂车间,技术员指着屏幕上的数字说“这精度,搁以前想都不敢想”;想起三次走进纪念馆,不同的人站在相同的展品前,眼里闪着一样的光。
路边有群孩子追着跑,手里举着小小的红旗,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。我站在原地看了会儿,突然觉得,这红色的火苗,从来就没灭过。从康家戏台的铜铃,到纪念馆的灯光,再到孩子们手里的红旗,一代一代传下来,就像水口山的矿脉,埋得深,却总在发光。
如今再想起没当成水口山工人的遗憾,倒也淡了。有些东西,比成为其中一员更重要——是记得那些红砖平房里的坚守,记得那些钢钎凿出的觉醒,记得自己从哪里来,该往哪里去。
抬头望,纪念馆顶上的星星灯亮了,一颗一颗,像极了当年忆苦窿里矿工们举着的油灯。这大概就是水口山给我的答案:所谓传承,不过是让昨天的光,照着今天的路,暖着明天的心。
上一篇 : 抗战指挥部成为红色课堂
下一篇: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”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顺利举办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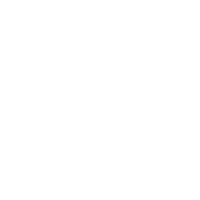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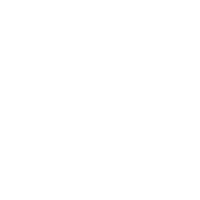
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42708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42708号